胡歌明星空间(我不能为了一个好的工作而放弃一个好的人生)
多年前,有幸现场观看了胡歌先生的《如梦之梦》。在莲花池中,胡歌很努力展现自己,随之,是久久不散的掌声。那一刻,想起他曾写过一句话:穿过莲花池,来到北舞台,被不绝于耳的掌声包围,恍惚感觉自己置身在一场大雨中,噼噼啪啪,噼噼啪啪。
如今的胡歌,因为《仙剑奇侠传》《琅琊榜》等作品和自身不同寻常的经历,被捧上了可能高于自己的位置。那些环绕身边的光环与掌声,何尝不像一场大雨。他置身其中,聆听内心的声音,寻求着与内心的和解。
那个本性内向的少年郎
《琅琊榜》里,是这样描述少年林殊的:雪夜薄甲,逐敌千里,奇兵绝谋,天骄之子,纵横往来有不败威名的少年将军,是金陵帝都最耀眼最明亮的少年。不少人对胡歌的印象,也是从明媚少年开始。
实际上,小时候的胡歌,与祖父母在内的5口人,挤在30平米的家里,没有自己的空间,一举一动都被无意识地监视着。胡歌本人也变得没有安全感,他喜欢独居,上海的巷弄,路边的梧桐,一天缓慢变化的光线与几个季度相似的风景,是最令人感到舒适的。
胡歌与猫有缘,也像猫,爱躲进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,不喜欢与人接触,见着陌生人永远躲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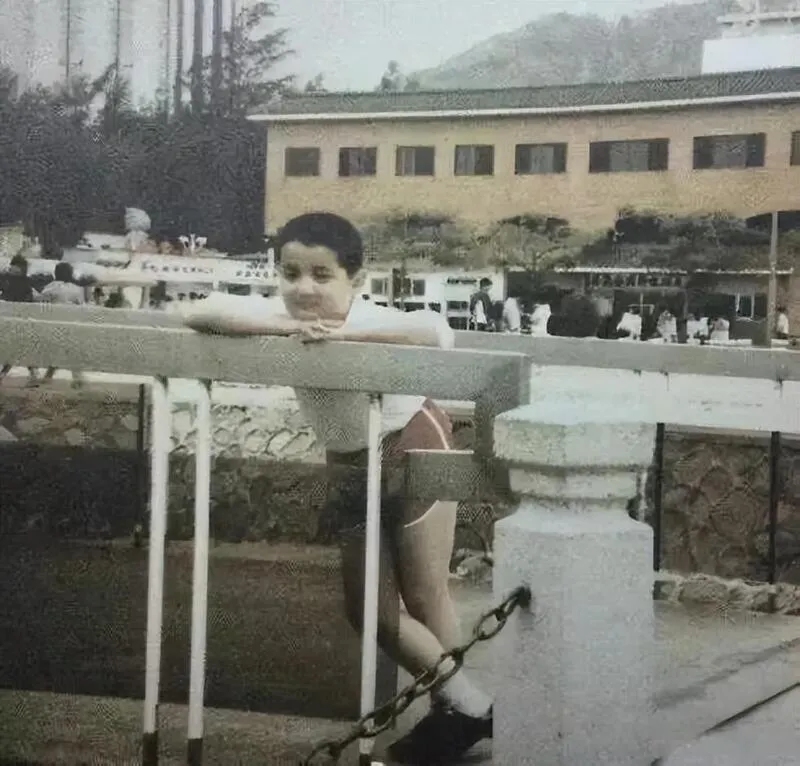
胡歌父母为了改变他内向且害羞的性格,送他去学习表演,这大概是他人生第一次突破舒适圈。往后,他在很多场合充分发挥学来的表演能力,也成为了校文艺骨干,升旗仪式主持人、校广播台台长、校戏剧社社长、校合唱团团长、班级团支书、班级物理课代表……
这些堆积如山的称号,使他像极了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小孩。
只是,长时间背离本我驱动自我,终会倦的。“这些抛头露面的活动,我没有享受,也没有不喜欢,因为小时候很听话,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天赋,因为我每次完成任务的时候都觉得挺累的,就是要花很多力气才能把这个任务做好。”
这也是内向人和外向者的根本区别——获取能量方式的差异。内向的人喜欢独自在安静的环境获取能量,倾向于了解事物的深度;而外向的人,喜欢在人堆里面获取能量,喜欢事物的广度。
胡歌曾在一篇《我们的故事》里写道:
“我骨子里的性格,并没有因为小荧星的这段学习经历而改变,但他学会了表演性格,表演开朗,表演阳光,学会了不再让家人担心。”
众口难调,人很难纯粹活出自我。我们很难再去探究最初的胡歌,究竟是真的热爱表演,还是仅仅在意家人的看法。唯一可以确信的是,小时候的胡歌,确实有一定的自律性和观察力,扮演得了一个活泼开朗且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
胡歌发小讲过一个故事,似乎做了很好的佐证。
儿时,一般的小男孩,放学后都是喜欢玩到太阳落山,父母拿着棍子来赶才回家。而每次四五点时候,胡歌就说要走了——我妈妈让我回家,我要回去做功课,然后其他人拉也拉不住。天边泛起了金边,少年郎胡歌就这样开开心心知足回家了。
这里也看得出来,胡歌与猫相似的另一点,天生有着讨喜的外观,偶尔从小盒子里钻出来舒展下筋骨,却十分依赖自己的小空间。
那个走上名利场的青少年偶像
二十来岁的胡歌,因为“李逍遥”,被捧上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,他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膨胀期:那个名为“偶像”的被乘数,与另一个叫“名利场”的乘数相乘。
当然,人们迷恋偶像的树立,正如期待它某天倒掉一般。
不久后,很多人也开始嫌弃他扮演的角色同质化。视觉疲劳的媒体,甚至反复拿车祸做爆点出通稿和宣传稿,八卦他与谁家女星暧昧的关系。这一切,都偏离了演员的本质。当大众对演员周边动态关注度,高于对其核心作品的关注度时,恰恰是这个演员最岌岌可危的时候。
大概2010年左右,胡歌模糊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。一条叫做“古装王子”的路线,随时等着他回去拥他为王,另一条路线叫“未知”,充满了可能与挑战。
大多数偶像派演员也知道往实力派转型的重要性,但这条路,远比想象中艰险。一边是利益集团赚快钱的希冀,另一边是自身亲身尝试后的挫败感。
胡歌亦是如此,试水了几部没什么水花的现代剧后,提携后辈的首个周播剧《轩辕剑》却火了。“这段时间我没有太大收获,感觉自己选择了一条不擅长的路” ,“我最想演的戏,就是演不到。”胡歌这段自嘲式的陈述,听起来颇显无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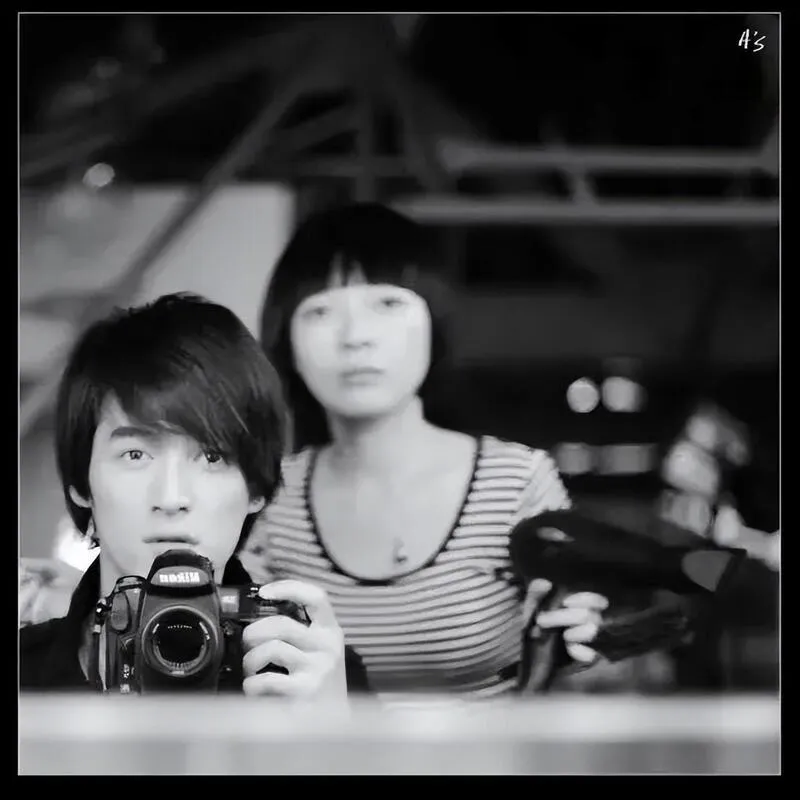
一般而言,优秀的演员分为两种,一种是体验派,一种是灵魂派。像是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,倒没有说谁更胜一筹。前者演什么像什么,诸如李雪健、周润发、张国荣、梁家辉大抵属于此列;后者能把自己的特性注入角色之中却不突兀,诸如李小龙、成龙、周星驰、陈道明等。
那时候正剧的制片组没找胡歌试戏,也未必没有缘由。胡歌并不算一个灵气逼人的演员。他的大多数表演,是踏雪有痕的。恰巧彼时的他,人生经历又略显匮乏,脱离他实际体验的角色,就扮演得有点“尬”。
幸运的是,他天性里带着些处女座的敏感。相比如演艺圈沉迷拉帮结派的老油条,他的赤子之心,让他时刻谦卑也惶恐着。这种面对世界的慌张,对演员来说恰是绝妙的好事。
因为敏感,演员才更易体察出别人不易关注到的细节,在荧幕上呈现角色时,也就比一般演员更有说服力。他面前的演艺圈,还有一些大师,同样是面对真实世界惶恐而又不安的人:卓别林、金凯利、周星驰。
To be or not to be,that‘s a question.之后的路,该怎么走,胡歌花了一段时间,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
那个避开镜头的青年演员
而立之年的胡歌,终于在某种意义上,学会了给自己做减法。
2013年,胡歌参加了场“守护斑头雁长江源之行”。彩云之巅,没有了镁光灯聚焦,胡歌那时候真的是抛下了自己的明星包袱,多了些行云流水,随意所至的洒脱。
他在四千多米的高山上拍照,与官兵互动,与藏族小伙打趣,还给当地的藏族小朋友上了节环保课。有张照片,他带着一群小朋友在操场上飞奔,那时候的他,是真的自在啊。
比起2010年,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表演力的欠缺。于是打足足够的力气,鼓起极强的心理承受力,去和经纪公司周旋,向过去的光环告别,走向了话剧这条纯粹的路。
他在《如梦之梦》长达八个小时的话剧中,学着理解生命的意义。他用了极为亢奋的态度对待了这个话剧,第一年他花了整整三个月,在北京的酒店式公寓和剧院,昼夜不停,反复琢磨自己的“五号病人”的表演细节。
“你一生中的迷,必须要用其它的迷才能解开,就像有的梦,必须穿过其他的梦才能醒来。你必须一个一个地走过,才能走出这场连环梦。”这是《如梦之梦》之中的台词,时光有许多似有似无的巧合,最后构成了人生这个大篇章。
之于胡歌,他通过扮演的“五号病人”,碰见了后来对他影响极大的两个人物——孔笙与李雪,也才有机会浴火重生,与“梅长苏”邂逅。
时光如果停留在2015年秋冬之际,那么胡歌的标签,大概就是不会白白活着的“梅长苏”——完美缺易碎。
幸或者不幸的是,后来《猎场》未达预期,让质疑的声音又出现了:“之前“梅长苏”爆红,是胡歌刚好碰到适合的角色。郑秋冬嘛,演得还是差点火候。”充满瑕疵的“郑秋冬”,把麒麟才子“梅长苏”从神坛拉落,让胡歌又要开始面对新一轮的挑战:如何演好身边的小角色。
质疑未必是坏事,杯满则溢,月盈则亏。有着空杯心态,才有机会装入新的东西。

其实文学史上,打动人心的,除了带着悲壮色彩的大人物,更多的也是贴近生活的普通人。
年轻时,谁不想做脚踏七彩云霞,身披五彩战衣的“大英雄”。年纪渐长,周星驰演起了《长江七号》中的民工爸爸,刘德华演起了《桃姐》中的罗杰少爷,李连杰演起了《海洋天堂》中的患病父亲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活成一部史诗,让作家把你的每一步抉择讴歌成诗,供人揣摩。生活把辛酸都揉碎了,夹在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中,优秀的演员,才能发现这些瑰宝,将这类小角色塑造得深入人心。
在2018年《朗读者》中,胡歌说出他的愿望,想由行云流水的令狐冲变成更有担当的郭靖。比起金庸笔下其他或天赋异禀,或智商过人的主角,郭靖无疑是最踏实的。
“梅长苏”之后,他急迫想给自己补点“普通人的生活体验”,为此打算休息一段时间。
曾有记者问他,空档期的时间,不怕错过一个好剧本吗?
胡歌如实回答:“怕啊,但我更加不能为了一个好的工作而放弃一个好的人生。毕竟我要活在现实生活中,而不是每天都在戏剧的梦里——况且,没有生活是做不好演员的。我觉得哪怕给我一个月、两个月的时间,哪怕我天天在家宅着都好,不会受到其他的影响和干扰,我可以持续地去做一件事。比如说可以把摩托车驾照考出来。”“还有比如把英语再学学好,比如说每个星期陪我爸去打几次网球,我这件事已经跟他说了好多年了,一次都没去过。”
他先去色达玩了一圈。其实,胡歌出行色达的计划很早就被人盯上了,但他后面先行把被盯上的摩托车撤出了色达,自己又暗度陈仓坐其他的车出城,然后偷摸着去了青海。
当然,天不遂人愿,胡歌的“普通人历险记”,终究被打断了。在赴美游学的时候,他学着“伪装者”,戴上一副宽边黑框眼镜,蓄起了胡须,还给自己剃了光头,扮演起了“自由摄影师”的角色。但仅仅三周后,他的伪装就被人识破,被迫开启了另一场“大逃离“。
这里也可看出,胡歌内心并不是那么强大,依旧容易被外界影响。在以“大逃离”为主题,游学回来的胡歌,选择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角色——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中遭人诬陷及通缉的逃犯,作为他的新起点。
那个感受生活的中年演员
从小荧星到南方车站中的“逃犯”,白驹过隙间胡歌走过三十多年的人生路。这三十余年,他也曾匍匐着,面过三次壁。
第一次,是他走进了小荧星艺术团的那刻,他学会了表演,扮演了别人认可的胡歌。
第二次,是他经历面容修复并拍完《射雕英雄传》后,他学会了怀疑,胆怯又小心翼翼地探索新的方向。
摄之旅。在《射雕英雄传》杀青之后,他疯一样地跑向远方,背后是欢腾的剧组,身前是漫漫的大海,他跑着跑着,自己就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车祸之后,那些顶着压力拍摄的委屈感、迷茫、无奈,仿佛一瞬间袭来,久久。
这次匍匐,他怀疑的是自己能不能承担起“演员”这个称号。从艺术宫的学习开始,胡歌就像一只漂亮的傀儡,一直被人推着前行的。所有人都告诉他,你很棒,你可以的。车祸之后,他内心有个声音:你毁容了,不行了,去做幕后吧。那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,却足以叫人胆战心惊。是否过去一直给予他自信去表演的,是好看的皮囊?
这时候的他,还没有明白自己的使命,没有活得通透。诸如周星驰、周润发、梁家辉老师,他们从小人物开始,跑了那么久龙套才得到的主角身份。那么蛰伏日子的不甘,那些对角色的渴望,都为日后真正理解进而扮演角色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而胡歌,在车祸之前过于平步青云的人生情节,充满了梦幻与玛丽苏成分。也正因为如此,他缺少处理无常世事、人情冷暖的大心脏,也缺少切换成配角视角,看待整体情节的视野。他并不是天赋异禀的演员,加之偶像派自带的光环,让他塑造角色时,缺少层次感,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。
而一旦支撑偶像派演绎的基石,比如好看的皮囊不复存在,也是他内心慌张的伊始。
如果皮囊难以修复,就用思想填满它吧。尚不清楚什么时候,他有了这样的体悟。但可以确信的是,这是昔日的偶像派,真正放下包袱的第一步。
这次匍匐,让他开始思考了自己的使命——做一个真正的演员,也为日后找到“自己认可的胡歌”,埋下了伏笔。
胡歌的第三次匍匐,是仰观宇宙之大后,他学会减少外界的干扰,坚定自己的内心。
一次公益活动,在人烟稀少的长江源,胡歌看见了冰川融水汇成的通天河,风的肃杀,山的壮阔。他扑通跪在草原,面前是茫茫的雪白一片,他沉思了久久。
这一次匍匐,已经距离上一次又有些年头了。人愈是懂得世间浩瀚,愈是理解自身渺小。
胡歌在一次演讲时说:”记得哲学家的英文单词是philosopher,本义是爱智慧的人。为什么不是有智慧的人呢?因为重点是这个人对哲学的渴求和探索。艺术也同样如此。”
这个阶段的胡歌,真正发现了自己对日常生活体验的欠缺。演员不是扮演角色的人,是理解角色的人。而被声名所累的他,脱离了古装剧,扮演的角色就会显得不那么接地气。
于是,他开始了自我的救赎,回归现实中,这次匍匐带来的思考:是如何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人一生最难演的角色,便是自己;最宏大的剧本,便是生活。这个骨子里不算外向的青年,这些年有太多的注目,太少的自己。因此,他有时也会不按常理的“逃离”,短暂的与自己独处。
他对此也有一番解释,“当你在创作的时候能做到忘我,当鲜花和掌声环绕的时候能做到舍我,当你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被广泛传播的时候能做到无我……那你就是真正的艺术家。“
即使喜爱他多年的粉丝,偶尔也会嫌弃一些他的不完美:晚睡,酒量差,韧性一般,偶尔孩子气,在感情上缺乏担当,时常还有些孤独症。抑因如此,打心底里,粉丝们会期望他早日脱单,有个人长久陪着他。
倘若数年之后,四十多岁的胡歌能和二十多岁的他有场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最好带着些新的身份:比如一名丈夫、一位父亲。像日常唠嗑一样,不再嘟囔着什么拿了这影帝那视帝的名号,而更多的唠嗑些柴米油盐,关心最近的状态。末了,最好再补上一句,人的一生是找寻自己的过程。
他曾演过一部村上春树的《品川猴》,在剧集里,他扮演了丢了名字的司机。他说,我几乎每天都活在别人的世界里,我的工作是成为角色的替身。我用他们的名字来替换我自己的。但他人剧本里即使再波澜壮阔,最值得花气力体验的角色,却是自己吧。
扫描二维码推送至手机访问。
版权声明:本文由网友在品度娱乐发布,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。如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,请与本站联系。(QQ:2861696926)







